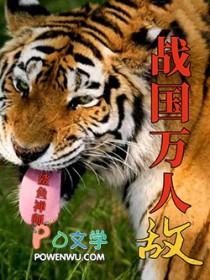SODU搜读小说>识魅 > 第266章(第1页)
第266章(第1页)
从谢萦失踪开始,已经快要过去二十天了。
那一天,谢怀月按计划出发,去找那几个躲在暗处窥视着妹妹的僧人。
他们租住在一处普普通通的居民区里,从始至终都没有以任何物理的方式跟踪过谢萦,这才能躲过这对兄妹的眼睛,不过最后到底还是被兰朔顺藤摸瓜地翻了出来。
可是在谢怀月推门而入时,那三个僧人正横七竖八地躺倒在客厅的地板上,都已彻底昏迷。桌子上的外卖还没凉透,水杯下面压着一张字迹俊秀的便笺。
——好久不见。
意识到这是调虎离山时,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
电话接通时,兰朔尚且不知发生了什么。听筒里的谢怀月劈头就问妹妹去了哪里,他诧异地转头望向不远处的露台,洒着金粉的花瓣还在纷纷扬扬地飘落,原本晴朗的夜空,不知何时已经蒙上了一层火烧似的红。
前后就这么几分钟不到的工夫,谢萦居然已经无影无踪地人间蒸发了。
最初的那段时间,两人一刻都没有合过眼。
妖魔与人类各有找人的手段,然而带走她的人显然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。
机场,车站,地铁,各大十字路口……偌大的城市里,无数的传感器和信息流连成了一张无形的天网,只要还生活在社会里,人就必然会留下痕迹,可是兰朔动用了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,却无法找到谢萦的哪怕一点踪迹。
朋友在电话里斩钉截铁地赌咒发誓,谢萦就算是长了翅膀,也绝对还没从北京飞出去。兰朔脸色铁青地接着电话,这时窗外大雨如注。
手机上正一连串地往外蹦着暴雨预警短信,一片异常的浓积云团正在城市上空快速聚集盘旋,暴雨就从这气旋里倾盆而下。
头顶天空阴云密布,暗沉如铅,远处地平线上却是一片金红,大片大片的鱼鳞云。这样奇怪的景象,许多人顶着大雨也要出来拍照,只是无人知道这并非自然现象,而是一个大妖魔正在以暴力冲击着一切可能存在的结界。
那时唤来暴雨的人就站在窗前,突然开口道:“是兰若珩。”
焦躁如狂也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,冷不丁听到他口中吐出这个名字,有一刻兰朔甚至以为自己是听错了,本能地脱口道:“你说什么?”
谢怀月微微转过头。
窗外闪烁的电光时而照亮他的脸,不知何时,他浅琥珀色的眼睛里,瞳孔已经变成了两条细细的竖线。这样冷血动物一样的竖瞳,足以把他平时优雅温和的气质打得粉碎,这样近乎冷酷的神情,对视时几乎会让人感到害怕。
“从前我没有把这些告诉你,是因为牵扯太深,对一个凡人来说实在有弊无利。”他淡淡说,“而且他已经销声匿迹了很多年,直到你们从三峡回来之前,我都一直不能肯定,他是否还存在于这个世上。”
接下来的叙述言简意赅,大概是谢怀月此刻根本没有粉饰的心情,也顾不及唯一的听众能不能接受得了这么大的信息量。
前情平铺直叙,当年多少深仇大恨、惨烈纠葛也都一句带过,听到最后,兰朔已经不知道自己该摆出什么表情。
“我们把他送到了杭州,从那以后的几年里,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音讯。”谢怀月微微沉默了几秒,又说:“再往后的事情,我也不完全清楚,从那时到现在的几百年,对我们兄妹都是完全的空白,直到二十年前他出现在小浪底,带着祭品,叩开了那座古墓的门。”
“那时我并没有和他照面,但有一点是确定的,如果他真的进了那个‘界’,就绝不可能再活着出去……后来的这些年,他也从未留下过一点踪迹。直到你出现,直到小萦翻出了那样的锦囊,我才能肯定,他依然活着,还在仇恨里蛰伏等待时机。”
兰朔半晌沉默不语。
带着家族的谜团回到中国时,他所寻找的“兰若珩”,并非一个蛰伏了几百年的幽灵,而是还不到三十岁的工程师giovannin——他的叔叔曾经有着极其完整的成长轨迹和人际关系,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份,除了一模一样的名字和长相以外,真的是同一个人吗?
还是说,那只是兰若珩用来在人类社会行走的一张画皮?
“我还不能完全确定,但很有可能从头至尾,世界上就不存在‘giovannin&039;这个人。”谢怀月也只是摇了摇头,“无论他是以什么方式活到今天,在这条路上,他已经比任何人走得都远,也许已经是从古至今无人可以想象的手段。”
兰朔脸色微微发白,再开口时,声音已经沙哑得吓人。
“他想做什么?他把小萦带走了……”
不管曾经多么潇洒威风,如今的谢萦也只是一个年轻的人类女孩,落在这样的仇敌手里,她会遭遇什么?她现在还活着么?
“兰若珩现在不会杀她,”谢怀月声音平静,琥珀色的眼眸里却凝聚了冰似的冷意,“否则他二十年前就可以动手。他筹谋了这么久要向我们报仇,不会仅仅只是为了杀人……我必须快点找到她。”
最后一句话的嗓音很轻,而玻璃窗里映出他半边面容,因为牙关咬紧,侧脸的线条显得异常冷峻,犹如刀刻。
整夜不歇的大雨持续了三天,气象局已经快要开始计划人工驱雨。凌厉的妖气将整个城市地毯式地扫过一遍,谢怀月最终肯定,妹妹现在并不在北京。
另一些消息正在接二连三地送到面前,比如谢萦失踪的红松庄园,产权恰恰属于那家扶持方国明起家、又在他死后夺走一切的基金——兰朔眉头紧拧地看完消息,仔细回忆自己和谢萦这几个月以来经历的一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