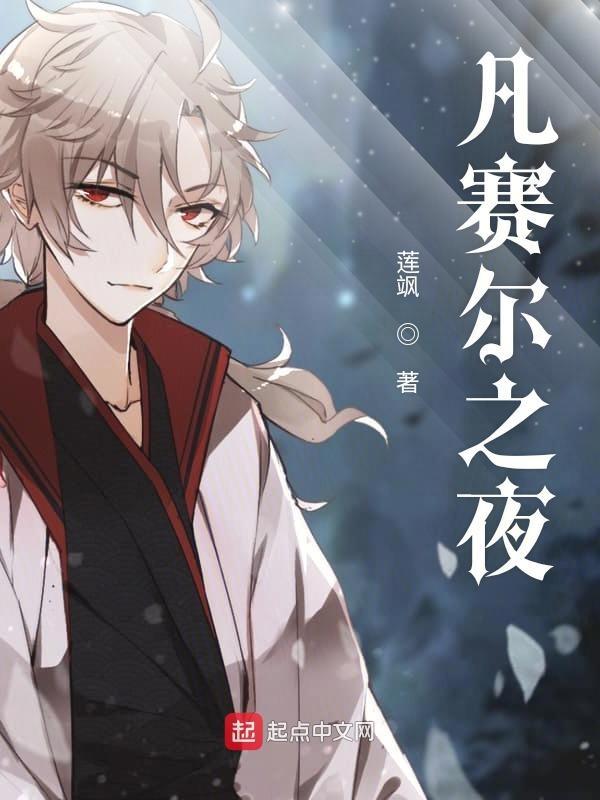SODU搜读小说>身为军校生的我不可能是虫族 > 第145章(第2页)
第145章(第2页)
“快逃——!!!”
掉马(下)
很多文艺作品里形容一个婴儿的出生,会说他穿过了黑暗的河,在混沌中看见了光。一个狭窄的出口,通过它,跌入白光之中。
于是一个新生命诞生了。
炽热的白光融化了希望,也融化了他的记忆,这段记忆似乎被熔断了,他只记得天罗地网般的光,无处可逃。
决堤般的白光淹没了他,吞噬了一切凄厉的尖叫,也吞噬了一切绝望的呼嚎。甚至在他的身体被融化之前,视网膜先被铺天盖地的光所填满,视觉神经仿佛也被熔断,晶状体也成了一个晶莹的玻璃球,只能折射出无穷无尽的光。
他看不见其他东西。
然后是天旋地转、疼痛和短暂的失明。
记忆再衔接上的时候,后背有些闷闷的疼,应该是撞击伤。但心口的贯穿伤却失去了痛感,他似乎在一个很狭窄的空间,被一些凹凸不平的、坚硬的东西所紧紧包围。他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艰难地伸手,指尖在心口处沾了一下。
濡湿的、铁锈味的、粘稠的液体。
伤口开裂了。
这样的伤口对人类而言就是致命伤,对虫族而言,只要在失血过多之前止血,就可以缓慢地恢复。心脏的瓣膜被身体组织的惯性复原,上面狭窄的刀口歪歪扭扭地对准,细胞不断分裂,像一个初次学习焊接的菜鸟工人,虽然焊接口丑陋,但好歹还是成功了。
现在的伤口是反复开裂的肌肉层。
奇怪,居然不疼。
燕屿眯着眼抬头,伸手摸索着环境。被强烈的光刺激,脆弱的人眼短暂地失去了视力,因此其他感官便凸显出来。他听见了沉稳的心跳声,一鼓一鼓的,就在他的后背,轻柔地与他相贴。
眼睛此刻才逐渐适应了光线,能够视物。他的手伸在透光处,看见指尖猩红的血液中,闪闪发光的鳞粉。
“……曼努埃尔?”
燕屿喃喃。
它怎么会在这里?
他一张口就被呛了一下,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嘴里盛满了血液。
“咳咳。”
鳞粉有致幻的功能,麻痹了他伤口处的痛觉神经。但身上的撞伤,因为没有开放性创口能够被鳞粉覆盖,依旧闷闷地疼。
这下他清醒了,好熟悉的感觉。
我是不是又被曼努埃尔抓在了怀里?
他慢慢恢复了知觉,察觉到自己似乎正处于一个失重的环境,有风从缝隙灌进来。而曼努埃尔则在急剧地下坠,在空中漂移压弯,腾挪闪避!
但更紧要的,是他嘴里浓郁的血腥味,那不是他自己的血,反而唤醒了他强烈的进食欲望。虚弱与饥饿让他胃部痉挛,渴望进食,渴望活着。
察觉到他的异动,蝴蝶甚至百忙之中伸出柔软的口器,把他往自己的伤口处推——这样紧要的部位,当然不会有人能够在不杀死它的情况下弄伤它。这是它自己弄破的,就是为了喂燕屿血,让他迅速恢复伤势。